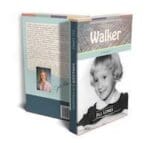如果我能说一说关于我的饮酒生涯的事情,那就是:很短。 但是还没有结束。 在电话转账之前,我与一位客户开始了婚外情。 在我的辩护中,至少我没有和所有人在一起。 但是只有一个。
他曾在我在丹佛拜访过的一家公司工作,尽管他不是我的主要联系人,但他是客户。 我结婚了。 我没有任何借口,但是我要说的是,我当年所做的一切以及随后的那两年,都属于“人们喝酒时做出的糟糕选择”的保护伞。
如果曾经有过婚姻有资格废除婚姻,我和斯科特就是这样。 这个过程既快速又容易,而且从权利上说,由于它已被废除,所以我什至不需要对此付诸行动。 但是通常我这样做是因为它发生了,斯科特是个好蛋。 我什至至少保留了他的姓氏,至少有一段时间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以一种崭露头角的年轻专业人士的眼光看待,而且我不想这么快就再次更改自己的名字。 这不是专业的! 另外,我正在为自己建立声誉,并希望获得连续性。 真是胡扯。
坎贝尔这个名字的奇怪之处在于斯科特一家人的发音方式。 一家人传闻说斯科特的祖母不想要一个以“骆驼”为韵的姓氏,所以他们不是像音乐传奇人物格伦·坎贝尔那样听到平常的发音,而是说“坎贝尔”两个字。
在和我的男友埃德(Ed)搬到芝加哥后,埃德(Ed)辞掉了在丹佛(Denver)的工作,与我在一起,我意识到我听起来像个白痴,以这种方式宣布我的姓氏。 但是,既然我以正常的方式说出来,我就越来越意识到这是多么的尴尬。 在吉尔的尽头,你的舌头伸到你的嘴巴上。 在Campbell刚开始时,它位于您的前下颌牙齿后面。 我越来越难以说出自己的名字,直到我讨厌这个名字。 这就是为什么在埃德和我一起下一步搬到亚特兰大之后不久,我将姓氏改为他的原因。 我不想回到童年时代的名字,而吉尔·哈德森听起来真棒。
那么,您会认为Ed和我一定做得很好。 我们没有。 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光充满了更糟糕的决定,这种决定源于青年时代和对酒精的初恋。 首先,我们养了一只小狗。 布罗菲是一个可爱的马耳他人,一个白色的绒毛球,看上去很像萨米(Sammy),但身上却长出了讨厌的保护性条纹。 他倾向于咬任何走过他选择捍卫的人的人。 如果他的体重超过四磅,我们可能不得不让他入睡。 回想起来,他可能只是表现出被他包围的一些沉默的愤怒和紧张。

Brophy以我们一起购买的房屋细分Brophy Farm的名字命名。 不久之后,我们又养了另一只狗,一只以埃德(Ed's)的吉普车CJ-7命名的金毛小狗CJ。 另外,大约在获得CJ的时候,我们住在亚特兰大的Habersham街上,当时我们家门口出现了一只小猫。 长大后,哈伯舍姆(Habersham)体重不菲,直到最终他将自己的名字变成了Shamoo。
我们一起在芝加哥买房,后来又一起购买Yamaha WaveRunners和一台60英寸的大屏幕电视(我们都买不起),这是我喝酒时思想发呆的主要例证。
我们买的那栋老房子理想地坐落在山顶上,可以欣赏到福克斯湖的壮丽景色。 位于芝加哥以北约一个小时的车程,这是一个真正的发现。 我的搬迁包涵盖了关闭点的成本。 我们怎么能 不能 买房子? 自从赖斯湖(Rice Lake)离开以来,这是我多年来住过的第七个地方。 我准备安顿下来。
我的父母来这里拜访,并花了几个小时帮助清理这个地方。 它需要它。 另外,房子有一个迷人的阁楼,我想把卧室放在那里。 问题是,弹簧盒无法适应楼梯。 没问题。 我父亲掏出窗户,砍掉了它们之间的支撑柱,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其抬起并穿过屋顶,并穿过现在足够宽的孔。 一旦修复,您几乎无法分辨出窗户发生了什么事。
仅仅一年后,当我开始觉得我的客户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那种客户时,我们会把那个盒子放在春天。 那时,我就职于另一家公司,Bee Chemical,这是一家用于注塑塑料的液体着色剂制造商。 这将使我脱离片状塑料的世界,进入模塑商的世界,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我在面试的前一天晚上已经和客户一起出去了,所以当我沿着丹瑞恩高速公路向南开车去公司位于芝加哥高地的总部时,看上去很粗糙,而且感觉也越来越粗糙。 Bee Chemical是《财富》 500强化工公司Morton International的子公司,所以我知道药物测试是新员工招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不过片刻,我惊慌失措: 等一下,他们会做清醒测试吗? 我不太确定是否可以通过测试。 是的,喝酒的事情一直在发展。
前一年,事情已经不止一次地失控。 就像我们参加Ed的朋友的婚礼的时间一样。 摄像头正变得越来越流行,我担心可能还有一些令人讨厌的镜头来纪念我短暂的饮酒生涯。 (这是我与宇宙的交易:请,如果您要打开该视频,还可以公开一下我们的pom-pom小队的镜头吗?)
但是,即使我遭受了种种痛苦,我也从未考虑过完全放弃饮酒。 每次爆炸后,由于我醉酒时的不可接受行为,我会躺下一会儿,时间会流逝,Ed会冷静下来,然后我们继续前进,逐渐将酒精倒入混合液中。
如果酗酒者不愿面对自己的恶魔,那么酗酒者的伴侣也没有什么不同。 人们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所爱的人是 其中一个。 当然,多年来,耻辱感一直在减少,我必须承认,作为一个清醒的酒鬼已经积累了很多年,这已经成为一种荣誉徽章。 但是,只要我这一辈子生活,关于酗酒的那部分就不会改变。 我就是那个那是我。 我控制的是保持清醒的部分。 但是住在芝加哥,我还没到那个门口。
当我住在芝加哥时,发生了另外两件事。 第一,我母亲独自一人来拜访。 爸爸又回到了酱料上,她就在自己身边。 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的身体状况可能比他差。 但是,我们俩都不值得该死。 向前走了两步,然后我便有了另一种巨大的情绪爆发。 我想知道我是否会发疯,我的意思是说,我真的是精神病患者。 那种愤怒和沮丧的可怕感觉,甚至只是想一直尖叫,这一点实在是毁灭性的。”
因此,她来了一次探访,需要一个周末摆脱疯狂。 这是我们结盟的机会,我想帮助她。 当然,当时我本人正坐在一条漏水的船上。 这是她那个周末对我说的一件事,我记得:“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承认这一点,但我希望我从来没有孩子。” 可悲的是,这不足为奇。
发生的另一件事是我与梅琳达重新建立了联系。 我母亲来访的那个周末,我们回到我的公寓里-这是埃德从丹佛搬到那里的几个月,然后在我的答录机上等着我,发现一个惊喜。 梅琳达从爸爸那里得到了我的电话,然后打电话给我。
自从大二后的那个夏天以不同的方式走以来,我们一直没有说话,所以很高兴听到她的声音。 在高中时,我们有类似的分道扬not,而不是说咒语。 两次,一切都在我身上。 梅琳达是鞭子聪明的人。 我很难与她的八年级数学考试成绩相提并论,而且我们俩都毕业于班级最高水平。 但是她也很可爱,在我看来,她过于依赖这一点。 就像她对她所有的人都没有信心。 她卖空了自己。
事实是,我很难看出她缺乏自信,因为我无法忍受看着它在我内心多么耀眼。 到那时我已经获得了一些外部成功,但是在这一切之下,我缺乏自信。 当然,这就是我们所有人要做的事情:我们判断并拒绝他人,因为我们不想看到的隐藏在我们里面的东西。 (当然,这就是使人际关系非常适合向我们展示我们的工作位置的原因。)
重新建立我们的友谊真是太好了。 圣诞节那天我们在莱斯湖聚在一起,我看到她怀了她的第一个孩子。 她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1989年初,我将与Bee Chemical一起搬到亚特兰大。 1989年XNUMX月,我在北卡罗来纳州探望客户时与她和她的年轻家庭度过了一个周末。
实际上,我是在她的家中探访的,当时我从母亲那里收到一条语音消息,说我父亲大约一周或更早又复发了。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每隔几周就和父母通电话。 到那时,我的雷达已经过微调,我通常可以分辨出什么时候复发了。 但是每次,我都感到震惊。
这次没有什么不同。 我看到它来了,我感到自己的肠子被刺穿了。 当然,这不是我和朋友谈论的话题。 那时,梅琳达(Melinda)目睹了许多情节-就像我们赛后去我家的时候,做了最好的绒球表演之一,却发现我父亲昏昏欲睡,睡在沙发上-但在功能失调的家庭中,秘密和沉默是密不可分的。 有趣的是,作为一名护士,梅琳达(Melinda)继续将自己的职业生涯投入成瘾和康复领域。
对她家的一次致命的拜访本来应该是九月的第一周。 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父亲的清醒日期是30年1989月11日。我的父亲是1989年3000月XNUMX日。我在回家的路上住在科尼利厄斯的假日酒店。 在任何一家酒店的酒吧里喝酒都成了我最喜欢的饮水坑,因为我不在城里-远离Ed的视线-而且不必开车。 到那时,对酒后驾车的危害的意识飞速增长-一张XNUMX美元的罚单和丢失驾照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正试图在快速发展的形势下自负盈亏。
所以我最后一次喝醉是对我父亲的反应。 当然,喝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酒鬼,这就是酒鬼的行为:他们喝酒。 我的男朋友对我的饮酒感到厌恶已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这次,我什至感到恶心。
漫长的夜晚,与酒吧里的每个人交朋友之后,站在酒店房间门前,我无法将钥匙锁上。 尿液开始慢慢流下我的尼龙,穿上我的高跟正装鞋。 对我来说,那是我的底线。 第二天,我躺在头旁边的床上,电话醒了。 但是当Ed试图到达我的时候,我没有听到它一遍又一遍地响起的声音,因为我意识到自己身体不好,因为我在昏倒之前就给他打电话了。 前台人员最终拒绝打通电话,因为它打扰了其他客人。
第二天早上,在与已经受够了的埃德(Ed)交谈之后,我打电话来寻找下一次机管局会议何时何地在我们家附近。 (是的,埃德和我一起在亚特兰大买了另一栋房子)。 好消息是我确切地知道需要去哪里。 那个星期三,我在克拉克斯顿的一次妇女会议上拿起一块白筹码,整个过程我都哭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喝酒了。
他们在机管局中说:“有时很快,有时很慢。” 我父亲选择了较慢的道路。 另一方面,我已经经历了他所有不幸经历的折磨,这使我可以直接跳到更快的方向。 幸运的是,我还有很多 s:我没有丢掉工作 但,我没有丢掉我的房子 但我并没有失去家人 然而, 尽管最后两个在边缘摇摇欲坠。 我当时喝醉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最好的想法只是让我走上了AA的门。 在到达坚实的地面之前,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有关我妈妈的各种附录 “我的父母来拜访,并花了几个小时帮助清理这个地方。”:首先要打开很多箱子,然后是Ed T.(吉尔的父亲),我开始从事一些真正的工作,从事一些主要的木工,墙纸,绘画工作。 真是太热了,没有空调。 吉尔(Jill)和埃德·H(Ed H.)不在工作,似乎不在乎我们在做什么。 Ed T.和我三天后终于放弃了,回家了,对这对正在工作的夫妻不加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