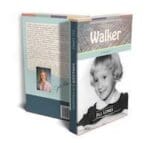我在Servantis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就是有机会再次与真正杰出的人一起工作,是杰克逊(Jackson),他于1995年XNUMX月出生。如果姓氏可以互换,中间名完全是一次性的。 所以里克和我选择对我们男孩的中间名做些好事。 为了给查理(Charlie),我们送给他保罗(Paul),以纪念里克(Rick)的父亲在我和里克(Rick)见面之前就去世了。 然后我们给了杰克逊一个中间名爱德华,使我的父亲感到惊讶。 想象一下,当杰克逊最亲近的朋友之一杰克逊·爱德华也感到惊讶。
那年年底,当杰克逊(Jackson)才几个月大,而我仍然在Servantis任职时,我在家敲门。 邮递员递给我陪审团传票,我必须签名证明我已收到。 “好奇怪,”我想。 “这些不是通常只是邮寄过来的吗?”
阅读这个大陪审团的传票(更正确地说,是传票)后,我注意到了时间要求:每周两天,两个月。 他们是认真的吗? 作为心脏病发作。 因此,我有两个月的时间,而不是在星期二和星期四去诺克罗斯,而是去市区。 在第一天,他们为少数人辩解,他们声称这将是不合理的困难。 50个左右的游泳池足够大,有一些摆动的空间。
当一切都说完之后,我没有回答关于我的想法或看法的一个单一问题,而是参加了由23人组成的陪审团。 “您是富尔顿县的居民吗?” 是唯一被问到的问题。 我们被挤进一个房间里,合影留念。 然后他们告诉我们演习。 每天,我们都会听到富尔顿县大约100件重罪的证据。 听到它之后,我们将投票起诉-“真实法案”-或否-“没有法案”。
我们是在电话中询问我们是否认为有足够的证据,以及该证据是否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以提出起诉。 据推测,在富尔顿县,被选为大陪审团的人是“该县最有经验,最正直和最聪明的人”。 这是一个满足可衡量标准(例如收入或大学学位)的人员的人口统计资料,表明一个人可能有足够的能力来完成这项任务。
警察经常是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的人。 一个典型的场景是这样的:“这是我观察到的,这是我逮捕肇事者时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们现在拥有的证据。” 基本上,如果大陪审团不接受他们的故事,那位警官的努力是徒劳的。
一整天,只要至少有16名陪审员一直呆在房间里,我们就可以离开并稍作休息。 我们将直接通过午餐直到下午中午之前结束。 (我实际上非常忙于工作,所以当我们完成工作后就直接去办公室了。)这是两名警察助理警察连续不断地游行,警察将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坏事。
一个月后,我们得知有一个特别的大陪审团在召集,很可能会这样。 自XNUMX月初以来,这个故事一直发生在当地的AJC中,当时有一个孩子被杀,一名警察在摩托车商店被枪杀。 我读过《今日美国》,只浏览了当地的周末报纸,所以我知道此事,但没有密切关注。
1996年1965月上旬,地方检察官刘易斯·斯拉顿(Lewis Slaton)提出谋杀,重罪杀人和对两名警察Waine Pinckney和Willie Sauls的严厉攻击的指控。 斯莱顿(Slaton)自XNUMX年以来一直担任亚特兰大DA,并将于当年退休。 那时我已经看到一个月的起诉书价值,无法开始猜测那个人所看到的一切。
十年前,当我住在费城市中心时,我与潜在的种族主义浮出水面。 我现在相信这是我一生能够治愈的东西,并且我取得了良好的进步。 诚然,我仍然生活在一个几乎每个人都是白人的社区,但是我和里克喜欢走到小五点(Little Rick),这是里克住过一段时间的各行各业的人杂乱无章的杂物房。地平线剧院的音乐剧。 我过着安全的生活,但不一定是庇护的。
陪审团本身可能是半黑的,我通常坐在一个高个子,醒目的黑人妇女旁边,每当一个名叫朱利安的军官进来作证时,他都会发出嘶哑的声音。 他是一个长得帅的黑人,通常穿着合身的黑色连身裤,曾在Red Dog部门工作。 (好吧,当他出现时,我也和我的邻居一起放了一点。)富尔顿县的大多数重罪都发生在亚特兰大最崎rough的地区,行话开始变得熟悉。
随着我们的服务开展,我注意到犯罪的日期通常早于一年或更早。 作为陪审员,我们被鼓励提出问题,所以我举手询问了这一点。 他们告诉我们:“这是系统达到发出起诉书的时间所花费的时间。” “许多人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甚至在很多之后,许多人都在庭外达成和解。” 因此,当我读到一个离家几英里远的谋杀案时,我很惊讶地意识到这件事是在几周前发生的。
尽管亚特兰大等大城市的种族紧张局势并不新鲜,尽管全国各地最近发生的事件已将事情推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水平,种族不平等是整个蜡像球支撑的一个问题。 我很天真地说我很明白DA Slaton的理解方式。 因此,我不知道所有驾驶员都在按照他的方式起诉这两名警察的决定中发挥作用。 但最重要的是,他竭尽所能追赶他们。
在一天半的过程中,我们听到了37个人的证词,包括直接参与其中的人,目击枪击事件的人以及进行内部调查的人。 我们从各个方面听到了证据,但与审判不同,审判中有律师帮助陪审员对案件进行梳理,这无疑是有偏见的,但仍然如此,我们只能尽其所能来理解事情。 我们被鼓励做笔记。
作为大陪审团,我们的指示是确定是否对犯罪指控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以确保将案件送交审判。 我们不仅在寻找大量证据,而且还在寻找案件是否受到有说服力的证据支持。 有一条学习曲线可用来解释这意味着什么,并且有助于将其付诸实践。 届时,我们将有大约800个机会获得成功(每天100个重罪,一周两天,一个月)。
当人们提供证据并见证人分享他们的观点时,有关Moto Cycles商店7月XNUMX日发生的事情的照片开始逐渐形成。 我有很多常识,足以意识到当故事彼此矛盾时,某个地方可能存在一些真理。
我们听到了所有证词,其中有些是矛盾的,有些是谎言,我内心的难题制造者开始努力找出最有意义的方法。 由于我是一名作家,所以我写了一个连贯的观点 我以为那天发生了什么,供我个人使用。
地方检察官斯拉顿(Slaton)有一个议程。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知道他有一个。 他对陪审团的指示之一是,在退回我们对真实法案或不法案的裁决之前,我们应该花很长时间进行审议。 最后,经过几个小时的审议,我们投票决定不起诉官员。
在提供证词和证据的消防水带之后,一些陪审员只想继续起诉,并让他们在审判时将所有问题都解决。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得不经历很多事情。 但是在我看来,我们没有被要求对是否存在 更多 证据。 我们负有确定案件是否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的责任。 由于DA将所有指控捆绑在一起,因此可以归结为: 是否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些官员犯有谋杀罪?
当我们的陪审员们在我们所谓的私人房间中审议此案时,对此进行了讨论。 我对此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并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有人要求我“站起来再说一遍”。 所以我站起来,开始重复我所说的话。 就在这时,房间尽头的一扇门打开,DA Slaton走进来。 什么?
他说他只是在检查我们,想看看情况如何,我们需要什么吗? 任何问题? “不,我们很好。” 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即我们应该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进行表决。 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对基本问题的简短回答很明确:绝对不是。
发布我们的决定时,没有伴随的解释说明我们如何得出这个结论。 我们被下达了恶作剧的命令,告诉我们如果与新闻界交谈,我们可能会被蔑视,或者发生某些类似的事情。 我在自己身边,知道真相远没有被告知。
出于内心对正义的渴望,我打电话给分配给这个故事的AJC记者朗达。 我对自己可能会产生的悲伤情绪有些偏执,我用电话在我家附近的Kinkos打电话给“匿名大陪审员”。 与我不同,里克读了整个AJC,他知道这个故事是一个充满种族张力的火药桶。 他根本不想让我打来电话,但他尤其不想让我在家打来电话。
隆达很高兴我成为一名十字军。 “我爱十字军!” 她已经乌鸦了。 实际上,当我试图将故事的真实事实传达给Rhonda时,她问的是:“陪审团的种族构成是什么? ?” 妈的。 那是我记得他们在大陪审团任职的第一天拍摄的照片的时候。 我家里有五个月大,一个三岁。 我不能冒险做或说出比我已经多的话。
回顾一下,我是来自威斯康星州北部的一位白人女孩,她非常关心两位黑人警官的公义,并想为白人警惕分子的行为提供帮助,因为后者在他们的肚子里开枪打死了其中一名,甚至不看他在射击谁。 我知道,论文中报道的几乎没有什么是真实的,或者是真实的东西被误导的土堆掩盖了,而当提供真相时,意图就变成了煽动局势的种族色彩。
三人被枪杀,其中一人死亡。 从我坐着的地方,发生的一切都与任何人的肤色无关。 再一次,似乎是一个白色的DA正在追捕两个黑色警察的女巫中。 坦白说,到结束时,很难说谁站在正义的一边,谁不在正义的一边。
看来,涉案警官的行为有点像牛仔。 在这一点上,我倾向于减少他们的懈怠。 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薪水相对较低,相对于我从事的工作,被枪击的几率很高。 我很感激这个世界上有足够的牛仔或女牛仔来承担这个责任的人。 但是,这并没有授予他们滥用职权的许可。
我经常想到,我能够拥有房屋和一小块土地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警察部队(保护我们的人)的有效工作。 这并不是像我可以像一个露营者那样把房子搬到我身边,所以我真正拥有的是与社会达成的一项协议,除非我说可以,否则没人可以进入这个空间。 而且没有人可以夺走或破坏我在这个空间中拥有的东西。 没有有效的警察队伍,这项协议将一文不值。 我的家将一文不值。 而且我在家里的安全性将大大降低。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防护服务中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就像我们遇到的任何其他不和谐一样,这总是一个要求了解更多真相的呼声,这是我们内心开始的。 我们必须寻找自己的种族主义主线,无论其形式或形式如何,都应与我们对权威的叛逆相抗衡。 然后,我们可以将注意力和对变革的成熟渴望转向需要解决的情况。
与大陪审团的所有生意都失败了一周后,我和里克(Rick)为查理(Charlie)举行了生日派对,并邀请了一个父亲,父亲是我曾与之合作的艺术总监肯(Ken)。 亚特兰大并不是一个小镇,但真实的说来,负责特别调查的助理DA是Ken妻子的兄弟。 因此,在聚会上与Nan交谈并不算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