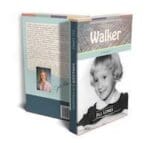莎拉的葬礼一个月后,我在按摩医生办公室见到的那个医士建议我读一本名为《爱,爱与性》的“ Pathwork”讲座。 这是在我与她分享我艰难的婚姻之后出现的。 我正在与这位治疗师共事的事实是一个奇迹。 那时,我是一名脊椎按摩师的常客,我初中时第一次去看脊椎按摩师,当时我的臀部突然跳出来,在体育课上跨着马骑。
我的男朋友蒂姆(Tim)买了一辆新摩托车,并为女友配上漂亮的新贝尔头盔后,第二次上大学。 但是,它的重量在我的左肩blade骨内部造成了背部刺痛。 当脊椎治疗师进行X射线检查时,他立即发现了问题所在:我的脊椎有一条曲线,将其向该区域的右侧移动。 然后他问我是否曾经发生过车祸。 不,我没有。
“这很奇怪,”他说。 “因为你也有鞭打。”
“我做?”
实际上,在pom-pom小组的所有这些年中,我们都是以精准为名,挥舞着相当不错的头。 说实话,我可能会成为一名中士。 当我在Data Transit工作时,我从一个同事那儿取了一个昵称,即匈奴吉拉(Jilla the Hun),他并不仁慈地坚持我的观点是,贸易展的摊位上不要堆满咖啡杯和其他垃圾。 (好的,所以我想一路上给了我一个绰号。)
大学毕业后,我在我居住的每个城市中都寻找了一个新的脊椎按摩师,否则我的脖子和后背将永远痛苦不堪。 这些年来,我所见过的不同医生的数量大约减少了十二位。 那时,我的脊椎按摩师琳达(Linda)也在巴巴拉·布伦南(Barbara Brennan)的治疗学校就读,她的朋友和同伴玛丽(Mary)也加入了她的诊所。
玛丽是一位动手医者,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但是琳达建议我去见玛丽,因为我想再次怀孕,琳达认为玛丽会有所帮助。 因此,我将与玛丽交谈,然后我将躺在她的桌子上,她将做任何能量治疗师用双手做的事情,在他们的指导下移动它们。 在很多次会议上,我躺在那里想着:“我不明白她在做什么,但我不认为她正在做这件事。”
有一次,当她把手放在我的骨盆上时,她问我在身体那个部位的感觉。 我不记得我使用过的确切字眼,可能是“冷”,“冻结”或“死”,但我记得看到过深灰色,于是我告诉了她。 她慢慢地工作,引导我想象一下刮掉那灰色的麻将它递给她。 在执行此操作时,我开始看到深红色的橙色。 我刮掉的灰色越多,在我的眼中就可以看到更多的橙色。 不久之后,我就怀上了杰克逊。
玛丽建议的演讲包含在一本名为“ 自我转变的途径 由伊娃·皮耶拉高斯(Eva Pierrakos)设计。 我读了整本书,立刻被这些教条迷住了。 AA计划的美丽之处在于它的简单性,但是我想要更多。 我还需要更多。 我已经准备好了。 在这里。 玛丽将我与一位名叫辛西娅(Cynthia)的女人联系起来,她是佐治亚州Pathwork的负责人,是Pathwork Helper的一员。 我通过电话与她交谈,她建议我加入一个由杰克(Jack)助手组成的小组,每两周开会一次以研究此材料。
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我将与杰克一起参加一个小组,每年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开会,中间有一年的休假,当里克和我搬家时。 我需要做很多工作的一个方面是围绕我作为女人的自我感觉。 我记得杰克曾有一次评论说我是个“美丽的女人”,但我无法接受。他的话像鼓鼓般跳到四分之一,让我兴奋不已。
我参加了一次会议,希望继续努力,避免再次见到父母。 这是莎拉去世的几年,而她的弟弟正在高中毕业。 当我们在会议室里走来走去时,小组中的其他人都在研究自己的深层问题。 一个人,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最近第一次与他的亲生母亲见面,一个女人最近在她姐姐死后在场。 “吉尔,”我随后走上汽车时对自己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大事,而你看到你的母亲不是其中之一。” 我去了布莱恩(Brian)的毕业典礼,很高兴能在那里看到他走过舞台。 有时,事实证明,我们的工作只是简单地将我们的头脑从驴子上弄出来。
开始Pathwork之后的夏天,随着我朦胧的内在景象变得更加清晰,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开始发生变化。 一方面,我进行了激光眼科手术。 我从二年级开始就戴着眼镜,当我还是一名高中生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眼镜。 不幸的是,我的眼睛一直很干燥,有时我的眼睛好像被人孔盖住了。 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春天访问密歇根大学时,医生注意到我红肿的眼睛,让我接受眼科医生的检查。
那年春天,我的联系真的困扰着我。 我很努力地进行夜间热处理,但尚未开发出一次性镜片。 我的镜片上积聚的蛋白质使干眼症变得更加严重,长时间的学习和随后的周末聚会对这种情况没有帮助。
因此,当医生将我的眼皮从里到外翻过来时,他印象深刻:“它下面看起来像一串葡萄!” 医学期刊上的某处是我的内外眼睑的照片,因为当教学医院看到这种极端现象时,他们希望将其捕获以供他人学习。
但是虚荣就是它的本质,而镜片的厚度就是它们的样子,一旦我的眼睛恢复了健康,我就继续戴隐形眼镜。 不过,在杰克逊(Jackson)出生的那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欧洲眼镜架开始流行。 尺寸非常小,它们是我的可乐瓶透镜问题的答案。 因为镜头越小,边缘越薄。
请注意,我尝试过以前版本的“新的,改进的,更薄的镜头”。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一种浸有铅的铅,以获得更高的折射率(因此,镜片更薄)。 他们没有受到打击,这就是原因:铅很重。 我用厚重的镜片换了鼻子上的凹痕。
在过去的三年中,我很高兴回到戴眼镜的地方。 因为当您有两个小孩和一份全职工作时,通常没有足够的睡眠时间。 睡不着觉,我的眼皮就像砂纸。 在Data Transit的办公室中,我将办公桌摆放在一边,以便坐在电脑旁时,我面对着门。 桌子的背面是一面坚固的木墙,所以有一天,一小会儿就睡不着觉-尽管我一生的礼节要到晚上10点才能熄灭-但我意识到我有一个完美的装置来做乔治Costanza。 我不止一次地坐在那张桌子下面的地板上,小睡了一会儿,这使我在下午的余下时间里生产力更高。 事实证明,戴眼镜只是走了这么远。
多年来,我一直在与眼科医生讨论眼科手术的可能性,他一直建议我等待。 他说,放射状角膜切开术有一些缺点,还有更好的技术距离不远。 1998年的夏天,我听说新的激光眼科手术已经准备就绪,黄金时段,眼科医生本人也正在为此做准备。 我得到了转诊,并且很快就进行了第一轮手术。
处于技术前沿的事情可能仍然存在一些缺陷。 当时,在第一次手术之后,需要进行第二轮手术,因为至少在我看来,随着眼睛的恢复,视力逐渐下降。 因此他们将我的视力改正为20/20,但是一个月后,我又回到了-3。 仍然比我刚开始的-10好很多,但并不理想。
即使在第二轮之后,当他们al愈时,我的视线还是有些后退,大约为-1。 我可以说这比医生走进检查室卖力卖药时所希望的要少:“太好了! 不需要40岁的老花镜,您几乎不需要50岁就可以使用它们!” 对此,他是对的。 我有第一个双焦点眼镜,我们可以称它们为渐进镜片吗?-在53岁。
相对而言,-1确实是个奇迹。 但实际上,戴眼镜仍然是我的一种痛苦。 我的头小得离谱,难以找到适合我狭窄脸部的眼镜。 那时,我还是成年人,挑选年轻的镜框并没有比我小时候做得更好。 大多数时候,我宁愿没有,也只能容忍一点模糊。 至少现在我醒来的时候可以在闹钟上看到时间。
几年前,我去DC时,我的眼科检查已经过期了。 由于眼球的形状变长,我有增加视网膜脱离的机会,这已引起我的警告。 然后,每年一次的眼科检查都需要用豪华的散瞳滴眼液使我的学生向我的耳朵敞开,这是使医生对我的眼睛后壁有良好观察的必要条件。
我的医生说:“您需要开始戴眼镜。”
当我的实际处方接近-3时,自动机器将我的汇率固定为-1。 差异反映出我的眼睛努力看清楚。 简而言之,我戴着眼睛。
因此,我去了乔治敦30英里范围内的每个镜架商店。 我注定要找到一个真正适合我的镜架。 我终于在孩子的那部分做了,所以我的颜色选择是青绿色,丁香色或淡丁香色。 我俯伏在国王的赎金下,穿着可以买到的最合适的鲜艳紫色眼镜走出Mykita。
激光眼科手术后不久,我参加了另一项选择性手术:吸脂术。 我的两次剖腹产以及我倾向于在下腹部携带脂肪-我相信这是对不喜欢做女性的一种反应-给我留下了只能被称为“猫挂”的东西。 认识到我们只需要忍受某些事情,还有其他事情我们可以做些事情,因此我选择了摇摆。
我所做的地方是在亚特兰大以北的郊区Alpharetta的办公园区内。 护士是一堆奇怪的东西,医生的年龄和山丘一样大。 我认为这是他的最后一幕,他只是想让它赚钱。 就是说,对于您可以开车回家的相当短的时间来说,这个价格是合理的。
结果并不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好,但是至少大部分的猫腻子都消失了。 因此,尽管事后仍然感觉不尽如人意,但总比对我的肚子一直生气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