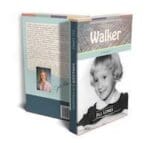第二部分更多的童年,青春期; 赖斯湖(1971-1981)
当我八岁时,我的生活变得举足轻重,我们搬到了北部12英里处的大城市莱斯湖。 在我们居住在巴伦(Barron)期间,我父亲从威斯康星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Superior)获得了音乐硕士学位。 我不能说我对此有任何了解,但是我们搬到莱斯湖时,他在莱斯湖的威斯康星大学-巴伦郡分校任教职,这是一所两年制的学校,是全州大学的延伸系统。 他会在那里教书直到退休。
我的母亲将离开在巴伦县法院大楼工作的秘书职位,并在莱斯湖担任一家保险代理公司的秘书职位。 我母亲的母亲多萝西(Dorothy)也曾在法院工作。 尽管她在结婚前几年曾在一间乡村乡村学校教书,但在我祖父母因42岁的爷爷中风而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农场后,我奶奶就当了秘书,这是由罕见的遗传性血液病引起的。
那时我母亲才17岁。 直到那时,自六岁起就学会驾驶拖拉机以来,她一直是帮助父亲阿莱努斯(Alenous)务农的关键。 一年后,当她嫁给我父亲后,她离开了农场,那里曾经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地方,后来他们上了大学。
我父亲比她大一岁,所以那时是大学二年级,而彼得仅在10个月后出生。 尽管我的父母继续住在为已婚学生定居的宿舍(实际上是古老的军营),但她并没有继续上学,尽管她是高中的直系学生,并且梦想着获得学位。 她的两个年幼的兄弟姐妹和我的祖母使农场尽了最大的努力达六年之久,然后终于不得不放弃了。
这种血管性疾病,即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导致在我祖父的肺部形成瘘管,在他衰弱的中风后,他们切除了大部分肺部以将其取出。 由于中风,他将在接下来的五十多年里with行,需要经常躺下以恢复呼吸,并在戴上帽子时流鼻血。 我母亲的两个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孩子也在这种出血中挣扎,但幸运的是,母亲没有患上这种疾病,所以我和我的兄弟也没有。
我的祖父母是严格的路德教徒。 在今天看来,我们可能会称他们为原教旨主义者。 瑞典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关系mixed昧不明,二战刚结束时,各方的强烈信念和偏见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母亲在高中时期约会的唯一限制是“他不能是意大利人或天主教徒。” 在一篇简短的文章中,母亲给了我关于她的生活的信息,她这样形容:
“我从小就固守道德。 这不仅是我们的房子,而且是那段时间的一部分,尽管我认为我们的房子可能格外僵硬。 现在甚至都很难想象,但是我没有被允许参加我们周五的体育课“跳舞”。 妈妈来到学校,和校长谈了跳舞的罪过。 那是七年级,我记得当时非常尴尬和非常困惑。
我可以参加广场舞/民间舞,但涉及舞厅舞时, 这 不允许。 因此,每个星期五我不得不独自待在场上,想知道同行们对我的评价。 我真的只是没有得到它。 跳舞有什么罪过? 但是你没有问。 刚刚被告知。
当我被要求成为大头菜节女王候选人并不得不拒绝时,我以为是因为可能会涉及舞蹈。 最糟糕的是,有人告诉我我不敢说我的乡亲不会放过我。 我不得不弥补其他借口。”
当天大头菜是该地区的重要农作物。 我父亲的家人长大了他们,坎伯兰镇举行了一个夏季节日,以纪念这种源自瑞典的蔬菜,这种蔬菜是白菜和萝卜之间的杂交种。 总是有如Rutabaga Festival Queen这样的事让我感到震惊,但是我很感激我作为一个年轻女孩的妈妈,如果能被提名为法庭,那将是我的荣幸。
她继续分享说,她的父母没有努力帮助她参加课余活动。 “我并没有被城市的孩子所避开,但是没有一种可以建立亲密友谊的方法,因为除了在学校,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过……父母无论如何都不会把你带进城里。 您乘公共汽车去上学,乘公共汽车回到家,然后呆在那里。”
她继续说这话,说她是50岁以下的孩子:
“我走到拐角处(1/4英里)赶上校车。 零下30度,比地狱冷,我只是穿了更多衣服,在头上缠了一条围巾。 汽车太难了,无法启动并将我带到那里。 乡亲们并没有真正告诉我,我只是知道。
在小学的时候,我不得不用吊袜带穿长袜。 在高中时,妈妈“让我”穿人造丝长袜-尼龙是稀有商品。 (但是,有时我会在门上抛弃它们。)女孩子们总是穿着裙子,在寒冷的日子里,你会在裙子下面拉一条休闲裤。 我想,放养业务很实用,但是却很丢脸。 其他女孩穿着鲍比袜子。 妈妈控制住了。 我只是在外面接受它而在里面死了。”
在我父亲关于他在农场长大的早期生活的回忆中,他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在房子的孵化器中饲养了小鸡。 每年春天,我们都会去镇上,捡几箱小鸡,然后将它们放入带有加热灯的起居室中。 看着这些小鸡真是太有趣了。 有一次,我的兄弟杜安·当当(Duane dang)在鬼混时跌倒,死于孵化器中,杀死了几只小鸡。 瞬间的蒸汽从妈妈的耳朵中喷涌而出,杜安认为他所知道的生活已经结束。
爸爸也做了他自己的猪cast割-是的!那是一个嘈杂的时期。 我不得不把猪放到膝盖之间,坚持不懈地维持生命,而他则用蘸有松节油的锋利的剃须刀作为消毒剂来完成这项工作。 猪没有那么多钱!
与父亲一起,我必须学习如何驾驭一匹马,如何将雪橇上的粪便拖运,将马匹和货车拖到干草装载机上,种玉米,耙耙,捡石头并拖运很多东西,所有这些都与马匹有关。 我知道我当时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乐趣,但现在我对这次体验深表感谢。
1950年代初的一天,父亲从树林里的一些工作中走回来时,告诉我他想如何增加谷仓并饲养更多的母牛。 他的故事令人难过,因为那时我认为他可以看到我很快就会离开,……有什么需要?
他正在给16-17头奶牛挤奶,这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 当妈妈在940年代中期患乳腺癌而我的姐姐Carol患了脊髓灰质炎时,他受到了打击。 这涉及他1937年的雪佛兰(Chevrolet)到城市的多次旅行,以及医生帐单。 隆德博士认为卡罗尔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夜晚是一个凉爽的秋天夜晚。 隆德博士开着他的新车出来了,他打开车门时灯亮了。 天哪,我们之前从未见过。
那是在1945年,我们仍在使用煤油灯。 救护车来了,爸爸骑着马进入城市,到了Sheltering Arms医院,并于当晚返回。 他有一个农场要经营。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醒来,从卧室的窗户上看到他疲惫而弯曲的身形,将罐头装在牛奶车上,然后去了谷仓。 他是一个疲惫,沮丧的人,我认为这折磨了他很长一段时间。 妈妈康复并长寿,但于1975年死于癌症。卡罗尔幸存下来,但再也没有走过路。
挪威人是坚忍,务实和常识的人。 但是他们确实有很好的幽默感。 例如,由于将柴火炉调高到加热煎蛋所需的时间很慢,我母亲会宣布“来一些干蛋”。 在特殊情况下,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一样,总是有着神秘的闪光。 他也可能发疯,讨厌,难以应付,我想我有时就是那样。
如果事情不顺利,他可以自己扑灭魔鬼的角。 在其他时候,他是最愉快和快乐的。 在教堂里,他总是坐在右边,妈妈总是坐在左边。 我一直以为他们彼此生气,但是我认为这是他们青年时代早期教会实践的条件。
我认为我父亲的教堂充满了日出和日落的美景,以及生长事物的奇妙之处。 他喜欢早晨的新鲜露水和农场的所有气味。 他爱他的马,但直到后来很多年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大约在1958年秋天的一天,我从大学回家。他说:“我今天运送了这支队伍。” 我说了一些非常聪明的话,例如“哦”。 从那时起,我没有任何想法和他谈过,并且对此感到后悔。 那两匹马和他一起长大,他和他们一起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团队,并且合作愉快。
艰难的一天结束后,我们将脱下他们的安全带,Cub和Bell将前往储油罐喝一杯。 然后他们会放牧草地,脖子抚摸着彼此,好像在说:“你对我很特别,今天做得很好”。